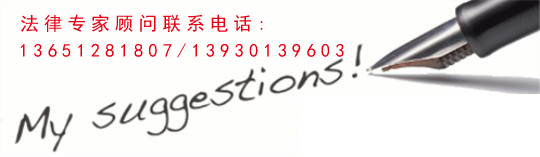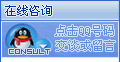近年来,我国毒品犯罪新情况、新特点不断出现,司法实践中不断涌现诸多疑难问题,针对毒品犯罪新动向,相关刑事立法也应进一步完善,以期更有效惩治毒品犯罪。
■针对制毒环节:补充和完善打击新型毒品犯罪立法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其中,传统毒品是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等已在全球滥用几十年的毒品;新型毒品主要指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类毒品,是由国际禁毒公约和我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管制的、直接作用于人体中枢神经系统,使用后会使人体产生兴奋或抑制,连续使用后人体会对之产生依赖性的精神药品,如冰毒、摇头丸、氯胺酮(K粉)等。通过化学合成的新型毒品获取渠道多且价格较低,导致我国吸食人员数量增长很快,因此危害范围更广。
近年来,新类型、混合型毒品(如冰毒和咖啡因混合而成的“麻古”)在中国不断出现,愈发多元化。公众对新型毒品危害普遍存在模糊性认识,滥用人员快速增多,特别是青少年盲目追求刺激,成为消费主体,涉案的新类型毒品比例连续几年持续上升,从东南沿海地区向内地扩散,形成制造、贩卖、销售、消费一体化。同时,走私、买卖易制毒化学品用于制毒的犯罪也在增多。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在惩治新型毒品犯罪方面,亟须补充和完善:
(一)对毒品应作含量折算。在新类型毒品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由于我国法律对毒品犯罪只作数量的规定,而无毒品成分含量的规定,使得法官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常常有“定罪容易量刑难”的困扰。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毒品犯罪分子为牟取暴利,以次充好、以假乱真,有时冰毒或掺假毒品的含量极低,甚至不到1%。由于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毒品不作含量折算,无法对未列入毒品但有毒品含量的案件定罪,就有可能出现罚不当罪的情况。毒品含量的高低直接反映贩毒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量刑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为了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公安机关在缴获毒品后,应当进行毒品含量的鉴定,以做到罚当其罪。对有证据证明大量掺假,经鉴定查明毒品含量较少,在处刑时应酌情考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2007年12月共同颁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特别强调:可能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毒品鉴定结论中应有含量鉴定的结论。
(二)对于醋酸酐、乙醚、麻黄素等制毒化学品犯罪,缺乏打击力度。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在打击制毒犯罪时遭遇瓶颈,即我国法律仅对制毒化学物品的走私、非法买卖行为给予犯罪论处的规定如刑法第三百五十条规定的走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而对在国内的制造、运输等行为却并不视为犯罪,这无疑增大了执法机关的打击难度。
■针对运毒环节:犯罪主体刑罚个别化
对于非法制造、运输易制毒化学品的行为,虽然我国于2005年发布的行政法规《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相应的行政处罚,但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随着打击毒品犯罪力度的不断增加,毒贩们开始采用迂回多变的毒品运输线路,绕道入境的贩毒活动十分突出。而且,毒贩藏匿毒品的方法不断变化,如利用货物、物品混装,溶解于液体中,利用动物活体藏带等。特别是近年来,以人体藏毒方式运输、走私毒品的案件较多。
在贩毒线路和手段不断变化的同时,贩毒人员也发生着变化。特别是近两年来大量涌现特殊人群毒品犯罪,即怀孕妇女、哺乳期妇女、艾滋病人员、青少年、老年人参与毒品犯罪的比例逐年增加。而我国对艾滋病人并不都具有独立的关押场所,对无年龄证明的青少年做准确骨龄鉴定还存在困难,对身患高危疾病的老年人也不适宜收押等问题给各司法机关打击毒品犯罪带来了困扰。其中,怀孕妇女、哺乳期妇女犯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在一些贫困山区,甚至出现了毒贩分子专门招募怀孕妇女的情况。执法人员也常常发现同一妇女利用怀孕、哺乳期,易名、易地多次进行毒品犯罪活动的情况。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对怀孕及哺乳期妇女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保外就医等方式暂缓收押,待暂缓收押的条件解除后再依法进行惩处。然而,这些人员多采取人体藏毒的方式运输毒品,人多量少,内部分工明确,且多受过反审讯训练,犯罪嫌疑人被执法机关抓获后,往往不透露真实住址、姓名,加之户籍管理中存在的不完善、执法机关跨省合作存在的经验不足等多方面因素,使得对这些人员的监视居住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执行。这些怀孕、哺乳期妇女在办理了相关诉讼措施手续后就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尴尬局面导致不法分子利用怀孕妇女或妇女利用自身怀孕、哺乳期间进行毒品运输贩卖,逃脱法律惩罚的恶性循环不断加剧。
针对这些特殊情况,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应当规范和统一怀孕或哺乳期妇女运输毒品的执法标准;同时,对于利用、教唆特殊主体特别是怀孕及哺乳期妇女走私、贩卖、运输和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刑法应当规定从重处罚。
■针对贩毒环节:注意固定、保全零星贩毒证据
近年来,虽然大宗贩毒案件在减少,但毒品犯罪形势依然严峻。毒贩们为了减少损失,多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贩运毒品,查获的案件中毒品数量多为几十克、几百克至上千克。零星贩毒作为贩毒行为的一种,构成犯罪的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论处。很多时候,由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对零星贩毒案件在证据上的认定认识不一,造成大量零星贩毒案件诉不到法院,只能作为治安案件处理,客观上对零星贩毒的日益蔓延打击力度不够。
实践中,对于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在审理中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个体现在定罪方面,一个体现在量刑方面。零星毒品买卖大都为单线联系,并且交易活动较为隐秘,公安机关对证据的收集比较困难;零星贩毒一般都是“一对一”进行交易,通常没有中间的经手人,因而无法找到第三者作为证人。即使当场抓获了贩毒嫌疑人,其卖出的毒品大多已被消费掉,实物证据已不存在,能够证明贩毒的证据只有购毒人员的证词和贩毒人员“一对一”的口供,证据种类单一,缺乏补强证据,导致定罪比较困难;在毒品犯罪量刑上,法律规定以种植、制造、运输、贩卖毒品以及非法持有的毒品数量来作为量刑的标准,而在零星贩毒犯罪当中,即使能够认定嫌疑人贩卖毒品的次数,具体数量也难以认定。
笔者认为,对于零星贩毒案件,公安机关在侦查时应注意固定、保全证据,特别是注意对言词证据的固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采用录音、录像方式对讯问和询问过程进行全程录音,防止行为人翻供或恶意诬告;同时,由于零星贩毒的最大特点是作案次数多,数量少,为了有效对贩毒行为人进行处罚,法律应当将零星贩毒次数规定为定罪量刑的法定情形。
■国际环节:加强国际禁毒合作堵塞多头入境
西南境外“金三角”一直以来是对我国危害最大的毒源地,所产海洛因和冰毒片大量贩入我国;西北境外“金新月”地区毒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西藏、新疆等地;同时,与我国相邻的印度、巴基斯坦是联合国批准的生产用于合法用途鸦片的国家,这些鸦片经过各种途径进入国际毒品市场,有一部分迂回进入我国,也有经尼泊尔进入我国西藏地区的;东北境外朝鲜半岛毒品、欧洲的摇头丸、南美的可卡因以及印度的氯胺酮也时常流入我国。此外,毒品犯罪的涉外案件不断增多,境外贩毒团伙加紧向我国输入毒品,国内外毒品生产双向流通,主要通过国内开办的地下制毒工厂,将毒品带出境外和将国外制毒配方带回国内,在国内生产。2006年以来,安徽、四川、广西等多个省份破获的制造冰毒案件都发现缅北技师到我国境内制毒或提供制毒技术的情况。
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国际禁毒合作,完善国际禁毒合作机制。在局部地区的若干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相对固定的、经常的禁毒国际合作。如2006年12月21日,云南省有关部门配合国家禁毒委官员前往缅甸克钦邦第一特区甘拜地与缅甸政府中央肃毒委进行会晤会谈。随后,双方组成罂粟种植联合踏查行动小组,先后深入缅甸密支那、八莫、南坎、九古等地对罂粟种植情况进行实地踏查。此外,在禁毒合作的过程中,除了正式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外,还应辅之以一些非正式的协议和具体的安排。例如,各级警官要定期联络,以便更好地解决法律适用和具体司法程序问题。(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