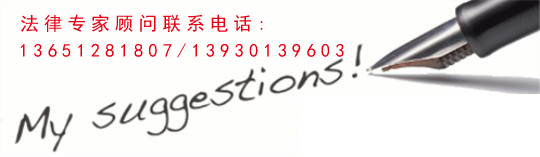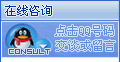近来,全国各地一、二线城市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中出台住房限购细则,落实中央关于房价调控的政策意图,笔者称之为“集束限购令”。其中“京版限购令”除了延续针对本市户籍人口的一般性限购措施外,对非北京户籍的人员购房的限制最为严厉,要求后者提供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北京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证明。纵观各地政策调整之手段,“户籍”再次成为杀手锏,在“限内”与“限外”之间刻画出明显的身份等级,刺激着人们对特权的联想和对平等的期许。北京市房地产协会相关负责人称“户籍限购”是必要措施,而且政策效果不佳的话还要加大同一方向上的调控力度。限购令的表面政策目标是限制房价,但其涉嫌歧视危及了相关政策工具的合法性,巩固并强化了特权城市和城市特权,在传统的城乡二元隔离之外增加了地区间隔离,不利于市场自由的扩展和公民认同的增进。
该项限购措施貌似“猛药”,但却并未击中房价调控(尤其是一线特权城市)的要害,反而可能抵消法律平等和政治认同上业已取得的初步改革成果。该政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值得商榷,限购令的功效与局限也需要反思。
户籍歧视:
从城乡结构到地区结构
京版限购令出台不久,北京的王振宇律师即向国务院法制办递交审查建议书,指控北京市新版限购令涉嫌户籍歧视。确实,限购令的政策要素包含“限内”和“限外”两个方面,户籍歧视至少体现在两点:一是购房数量限制上“内”“外”不平等,户籍人口可多购一套住房;二是对无住房的非户籍人口提出了“5年”的严厉限制。王律师向国务院法制办递交审查建议的行为不太可能得到积极回应,因为北京市的限购令正是对国务院房价调控政策的落实,可能失之严厉,但政策目标是一致的。
以户籍作为政策工具在共和国的成长历史中并不罕见。在毛泽东时代,为维护林毅夫所谓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城乡二元结构获得了体制化,“城市户口”意味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福利保障,而“农村户口”则意味着“禁锢”。改革开放通过对农民的土地经营放权和自治放权,实现了农村生产力的恢复和农民政治素质的提升,然而这些改革仅限于农村内部资源存量的结构性调整,尚未涉及城乡平等问题。城市发展与农民工进城将城乡平等问题正式“问题化”为我国政治和宪法上的严峻问题。“同票同权”、“同命同价”就代表了平等的时代呼声。户籍制度遭受批评的主要维度就是这样的城乡结构。
然而,限购令提醒我们,户籍歧视不仅针对农村和农民,还在城市之间构筑起了新的樊篱。限购令的有效规制对象并非那些在城市没有购房预期的农民工,而是相对于一线城市的那些二、三线城市的中产阶层。以往的“购房入户”毕竟还确定了一种相对明确的户籍获取条件,现在的限购令则从户籍现状出发限制购房。现在的关键已经不仅仅是你出生于城市还是农村,还包括你出生于哪个城市。在一线“特权城市”的决策者眼中,二、三线城市只是“更像”城市的农村罢了。以往我们愤慨于上海人歧视一切地方来的“乡下人”,现在这种歧视则在房价调控的“政治正确”之下将既有的歧视予以扩充和强化。
限购令反映了城市群内部歧视的“地区结构”的凸显,其背后是一种单向的“地区歧视主义”(地区保护主义可能是双向的),这对于进行改革顶层设计的决策者们应具有警示意义。
特权城市:
高房价的真实因素之一
此次从中央到地方的“集束限购令”的直接原因是高房价。房价居高不下有着各种复杂的体制和市场原因,不同人士会根据自身偏向的原因提出不同的对策。笔者这里尝试提出“特权城市”这一概念,作为分析高房价的因素之一。
所谓特权城市,指的是北京、上海、广州之类的一线城市,它们通过历史积淀和体制安排的方式获取了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资源与成就,且通过户籍福利的方式保持城市户籍人口对发展成果的独占。特权城市的高房价不完全是市场因素的结果,还有“超额福利”型特权的作用。比如高等教育领域,北京市名校林立,尽管是教育部直属,是全国纳税人供养的事业单位,但对北京市户籍子女的招生比例远远超过地方。著名宪法学者张千帆教授曾主持过高考地域歧视的研究课题,从理论和政策的角度深入剖析了相关的成因与状况。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价被“推高”,所反映的正是“购房入户”的政策安排所承诺的“超额福利”。为了子女教育,地方各路诸侯,无论出身职业如何,均举全家之力在北京购房入户,他们所购买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房地产,而是北京市的“超额福利”。因此,是受到体制保护的“超额福利”而非房地产本身的市场价值在支撑北京的高房价。从公平性上讲,“购房入户”毕竟有明确的市场标准,其政策正当性要超过目前的限购令。
特权城市的“超额福利”是高房价的真实因素,因此调控的方向就不是撕开法律平等的薄纱而重祭“户籍”利器,而是反思这种“超额福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种“超额福利”的形成,在其历史根据上不仅仅或主要不是北京户籍人口的贡献,因此其成果也不能被北京户籍人口独占。毛泽东时代的财富积累模式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计划体制,“户籍”的意义早已超过了简单的人口管理,而成为盛装“特权”的巨大容器。改革开放以来,户籍福利在社会平等化改革的进程中逐渐松动,但其中包含着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激烈博弈。限购令重新充实了“户籍”的特权与福利内涵,与改革的分享逻辑之间存在紧张。可以预料,这种“毒性”极大的严厉调控不仅效果难以持久(因为这是治标不治本,最终还是要回到常态化的市场机制之中),而且会产生极大的副作用,比如再次动摇人们对市场自由、社会平等和政治认同的信心。
针对支撑高房价的“特权城市”因素,正确的政策思考方向应该是如何合理拆解那些“超额福利”。例如,北大清华这样的全国性名校取消招生名额的地域歧视,实现平等竞争和公平招生,则穷举家之力来京“购房入户”的地方人士就会有更加理性的投资思考和生活安排。拆解“超额福利”不是要取消那些特权城市的所有福利,而是让其恢复到法律和公众可接受的合理水平,重点是拆解那些因历史和体制惯例而不合理地归属于市民福利的相关内容。拆解允许一线城市保留部分只针对本市户籍居民的合理项目。更宏观地讲,特权城市还根植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应着眼于地区平衡发展的结构性设计,包括分散超大城市的功能、调控地区间发展的互补结构、在政策与法律层面不断释放公平机会并确立平等规则。
改革的政治理性:
“身份”与“契约”赛跑
户籍是很重要的“身份”控制技术,一度成为改革的对象,但却始终难以消解或转型。英国著名历史法学家梅因在其《古代法》一书中将法律发展过程概括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身份”是特权的标志,来自传统的政治概念和技术系统,以区分为前提;“契约”是自由的标志,来自古罗马法,以平等为前提。梅因概括的法律史规律实际上也是政治社会史的规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自由的发展和国家政治法律结构的调整,其基本逻辑与发展主线正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进化线路,如不断释放身份束缚和特权空间。在改革30年“一起做大蛋糕”的过程中,由于大部分群体均能从发展中获益,而且平等观念和权利意识尚不发达,一些性质“严重”的歧视被“无知”地容忍了下来。但是,随着改革转向强调共享与公正的分配领域,改革初期的默契就被打破,特权群体希望借助一切政策机会和法律漏洞来巩固自身利益。如何巩固呢?第一步,确立具有“政治正确”性质的政策问题(如高房价),描述甚至夸大其严重程度;第二步,采用传统的身份识别与控制技术(如户籍)达到“排外”的目的(比如通过限购令推高房租价格,逼走在京“蚁族”,压制京外人士来京预期);第三步,利用房市的价格刚性和周期反弹,不断延续或重启身份性调控。
我们看到,在改革新的三十年里,围绕社会公正与个体自由的问题,很可能出现“身份”与“契约”赛跑的现象—这就是改革中的反复现象。政策调控往往没有从从长效机制和公平政策的角度着手,这次的调控重新打开那只名为“户籍”的“潘多拉之盒”,所迟滞和干扰的正是改革以来的“契约化”逻辑与进程。限购令所折射出来的政策设计者的“身份崇拜”表明其并没有理解改革的“契约化”逻辑。
上面所论的“契约”尚为一种私人间的自由契约。还有一种更加重要的“契约”,即社会契约。以社会契约为基础,我们通过宪法建构公民对国家的现代认同。这种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的根本所在。限购令的政策效果可能会撕裂此类认同。现代政治必然是认同的政治,而不可能是管制的政治。特别是在全球化和高流动性的当代,如此严厉的、缺乏理性基础和公正内涵的“身份”政治,其公众认同度不可能高,而且有悖于改革以来的“契约化”共识。限购令可能不仅仅是房价调控,而且还是人口调控—重新“身份化”的政策出台容易使人产生改革有倒退的联想。
总之,限购令警醒我们,对房市的基于户籍的调控在形式上违背宪法平等原则,在实质上偏离了支撑高房价的“特权城市”因素,将歧视扩延至地区之间,而且通过重新“身份化”来修正改革以来的“契约化”共识,抵制社会正义所包含的自由与公平的规范性诉求。更要命的是,针对这样的“复辟”之举和行政权力的强势作为,我们竟然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从而彰显出我国政治建设与法治建设对改革的共识原则及公民权利的捍卫能力之薄弱。如果此类政策断断续续、遮遮掩掩地得以长期化,改革其他领域取得的整合性与公平性成果将不断地被抵消。政策的出路之一可以是回归改革的共识理性,坚持“契约化”逻辑,弱化作为身份政治关键技术的户籍控制,拆解特权城市的超额福利,侧重保障性住房建设,宏观设计地区间平衡发展规划,真正以一种“包容性增长”的立场来设计、检讨与调整改革深水区的关键性政策。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